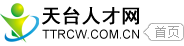韫玉含辉感动我心扉
2009-02-24 09:01:35
阅读量:1135
来源:天台人才网 作者:天台人才网
一方斗室,一张书桌,一位鹤发童颜、谈笑风生的老人……在我的印象中,陈瑜老师一直是那么勤勉博学,那么精神饱满,那么健步如飞———似乎,病痛是与他无缘的。
谁料,2004年春天,一个朋友突然告诉我听闻陈老师住院了,具体病情尚不清楚。难以置信,真的难以置信!陈老师向来健硕,怎么会生病呢?当时我就打电话给陈老师,陈老师确认了这一事实。我随后就赶到医院,见到了躺在病榻上的陈老师。“人有旦夕之祸福!”见了我,陈老师开口就说了这句话。“陈老师,权当累了,休养一回。”我接话,以为陈老师只是累着了。“得了脑血栓,左边的手脚已经不能动弹……”造化弄人?一年前,陈老师还亲自背着厚重的摄影架,邀我一同前去考察泳溪“廿八市”,翻山越岭脚下生风,让人丝毫看不出他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了。无法接受,真的无法接受!然而,陈老师的话语里透着乐观,心里还挂念着那本即将付梓的关于天台山文化研究的书。陈老师是累垮的啊!我默默祈祷,期盼着奇迹将来在陈老师身上悄然出现!
于去年初冬的傍晚走进中山东路的通德门,我又前去拜访陈老师。一如往日,陈老师正伏案书桌。见到我,陈老师放下手中的书卷,用熟悉的朗朗笑声欢迎我的到来。随后,我们愉快地进行交流,陈老师的谈吐依旧是那样地中气十足、幽默风趣、犀利深刻。临别前,陈老师赠我一本他在病中编成的新著《山地存稿》。没错,人在病榻上的这几年,陈老师始终不曾远离他所钟爱的文学事业。悉心拜读陈老师用心血凝成的《山地存稿》,发现当中既有陈老师对我县文学创作现状的分析与展望,也有对文学创作理论的精辟见解与积极探索,更有对我县曹天风、陈邦远、陈镛、胡明刚、余跃华等知名作家著作的文学评论,字里行间倾注着陈老师对我县文学事业数十年如一日的深情。
捧读着《山地存稿》,思忆着陈老师对诸多文学爱好者的奖挹与指引,我恍若回到了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在天台县城求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聆听到陈老师主持的文学讲座。我至今依然记得陈老师的一句话——文学即人学,从事文学创作首先要学会做人。此后,在兄弟学校文学社同人的引荐下,我带着自己稚嫩的作品前往中山东路陈老师家中,当面向陈老师请教。陈老师将我们引进古朴静谧、书香氤氲的书房。“你姓胡,可认识胡善林?”“他是我祖父。”“难怪看到你就觉得有些面熟!你与他神似更甚形似啊!我与你祖父解放初就认识了。他也是会写文章的,从政前与我同在刚刚创办的天台报社工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的文章写得很有个性。”一番寒暄,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而对于我的文章,陈老师大加赞许,这让我受宠若惊。当时我的文字其实难免稚嫩,陈老师以一个长者的宽博呵护了我这个晚辈的写作热情。此后我毕业回老家工作,但每年总要带着拙作,或是走进通德门,或是前往天台县文化馆,请陈老师赐教。陈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与我交流,分别时总会赠我几本文学刊物,并鼓励我坚持写作,使得当时身处大山的我能够借助文学的方式与山外的世界建立另一种联系。
在陈老师的感召下,我至今仍然虔诚地坚信文学的力量是强大的,它能够支撑脆弱的血肉之躯勇敢地面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陈老师在遭遇了病痛的折磨后,正是用他的行动诠释了何为“文学即人学”。
记得那时陈老师已经回家养病,我前去探望。坐在床上的陈老师依然那么精神,尽管左臂左腿已经不能受大脑灵活支配。陈老师笑谈自己现在走路时是独臂英雄,因为主要靠右臂支撑桌面走动。陈老师还是那么乐观,他说今后必须在沉默中爆发,否则就要在沉默中受折磨。所以他总是尽量硬撑着多活动,还与我相约他日共登赤城山、再观泳溪“廿八市”。
2004年年底,我刚刚从江苏昆山游历归来,卸下行囊就前去拜望陈瑜老师。奇迹出现了——陈老师正一个人费劲地借助拐杖上楼。我要扶他,他说不必。我发现陈老师已经能借助拐杖走不少路了。陈老师的气色不错!他说现在要跟另一个自己作抗争。言谈间,陈老师回想起1997年也曾去过昆山。他对那次昆山之行记忆犹新,谈起了天台乡贤庞亨福的热情,谈起了昆山名人顾炎武的伟大,谈起了阳澄湖畔的玄武石,谈起了沙家浜中的芦苇丛……陈老师的谈兴甚浓,我静静地听着。回来的路上,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健步如飞的陈老师。
2005年开春,又一个奇迹在陈老师身上出现了。陈老师在我们的陪同下,像往年一样来到滩岭花桃赏梅。花桃的外渚真是一处赏梅的好地方,满山的白梅,不时冒出几枝红梅。陈老师故地重游,兴致也好。梅花点点之间,陈老师谢绝我们的搀扶,自己借助拐杖漫步其中,令人心生敬意!我不禁想起咏梅的佳句——“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
2006年年初,我又去看望陈瑜老先生。他虽行动不便,但精神总是那么饱满。一见到我,他便连连感谢先前参加文学协会年会时我送他回家。谈到写作,陈老师提醒我要惜时,时间宝贵,不容浪费。陈老师希望我趁年轻多动笔,平时要像农业专家挑选良种一样,从生活中撷取创作之花,哪怕这朵花最初只是一个蓓蕾。
一如对我的叮嘱,休养在家的陈老师就是一直耕耘在“文学山地”上的老农,对文学的热情始终不曾冷却。每次碰面,陈老师总会和我畅谈文学,分享阅读与写作的心得。回想去年初冬的那个傍晚,期间陈老师与我谈起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陈老师站在作品比较的视角指出,与白朴的《天净沙秋》相比,该曲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意象指向的集中。我也认为该曲的精妙之处在于不仅仅停留于意象的大量铺陈,而是在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之时,一句“断肠人在天涯”喷薄而出,将郁积的悲凉展现得淋漓尽致。陈老师听后点头称是,并告诫我:“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是富含情感张力的,能够引发读者共鸣的。小胡啊,我们进行文学创作,应当同时站在作者和读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作品。惟有如此,方能精进。”
告别时,夜色已经深沉,我手捧着陈老师的《山地存稿》走出通德门。夜色掩盖了台门上“韫玉含辉”四个大字,另有一分感动直抵我的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