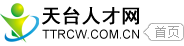心中只有一根弦
2009-07-27 08:23:57
阅读量:483
来源:天台人才网 作者:天台人才网
听朋友说起他们村子里的事,让我动情的是一位14岁就当家立计的老农故事。
他叫张兴华,今年77岁。就像平桥镇东岙村后山上的一棵老松树,长在悬崖石缝中,不屈不挠、默默无闻地顽强生活着。长长的63年,他顶着严寒酷暑,挡住暴风骤雨,保护着他脚下的小树茁壮成长。走在村民群中,你难辨认他,兴许在一转眼之间,他就消失在你的视野里。

十四岁当家立计
1946年,张兴华在杭州当司机的父亲中年病故,丢下最大只有十六岁,最小年仅两岁的两女三男五个孩子和长年患病的妻子撒手人寰。顷刻间,一家断了支撑的栋梁,村里亲族邻里纷纷叹息:一个有病的女人,五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这六口之家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这一年,作为长子的张兴华才十四岁,正在邻村小学读三年级。家庭的突然变故像天塌下来一样,一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孩子被惊呆了,从此他失去了本该属于他的快乐欢笑。十四岁的少年,不得不像成年人那样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家庭。
这真是个懂事又有强烈责任心的孩子,他没有过多地沉溺在悲痛之中,他和姐姐商量在绝望中寻求生存之路。他要用柔弱的躯体来替换家中断了的栋梁,千万不能让这老屋坍塌下来,否则多病的母亲谁来照顾?六个人以后怎样生活下去?于是他断然放弃了继续上学求知的机会,用稚嫩的双肩来挑起这副生活重担。他决心要像父亲那样承担起赡养母亲,供养弟妹上学的责任,最苦最累也要舍命陪一回。
全村最勤劳的人
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挑起六个人的生活担子,完成三四亩田地的劳作,也非易事一件,更何况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但懂事的兴华自有一番对应策略,他和十六岁的姐姐作了具体分工。母亲有病生活需要照料,递茶端汤要细心周到,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要人调教,这样的家庭细活姐姐最为合适。农活要力气还要讲技术,非他男子汉莫属,于是起早摸黑就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十五岁的他居然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一个下着春雨的早上,他披蓑戴笠牵牛去犁田。一个过路人到这里不认路,正好兴华扶犁往田那头耕去。那人见一个蓑衣笠帽的农人在干活,就扯起嗓门喊道:“老伯,到风门岙往哪走哇?”等兴华调转头来回答时,路上行人才看清自己问的是一个比儿子还小的孩子,不由得竖起拇指说:“小弟弟,看不出你小小年纪就这样有出息,怎么不是大人来干这样劳力的农活呢?”听完兴华的诉说,那问路人又是一阵由衷的称赞:“小兄弟,真难为你,谁家姑娘以后嫁了你这么好的青年,定然三生有幸。”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风霜雨雪,严寒酷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几乎没有一天闲坐在家,谁有事找他,总在田头地边。村里人没有一个不夸他的。邻居要教育孩子,总拿他作榜样说,“看看人家兴华,十四岁就代父出力,一个人忙进忙出,什么时候待在家里玩过。”为了种好三四亩田地,他要抲犁操耙;为了能养活一家,他要锄草施肥;为了争赶农事,他要起早摸黑。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别人在家天南海北闲聊歇息,这种时候正是兴华在家整理农务家事的时光。把家里的柴株、柴段劈细,姐姐可以省点力气。猪牛栏坏了,趁雨天修理一番。大簟方箩的小漏小洞,自己动手补上几根篾丝,省得用时慌乱。
农忙前后,兴华稍空了就把家里的人畜肥一担一担往外挑。他种的田地庄稼长得绿油油,收成总比别人好。后来入社立队就一直被大家推选当生产队长,一干几十年。
悉心培养两个弟弟
父亲病故时,兴华的二弟十一岁,刚上学不久,小弟才两岁。作为长子,他义无反顾地担当起父亲的责任。他把二弟送到屯桥读小学,二弟从小聪颖过人,自然理解大哥栽培的苦心,读书格外用心。小学毕业就考上平桥育青中学(平桥中学前身),从初中开始就享受助学金,三年后轻松考上天台中学,1954年顺利考上安徽农大,成为当时周围山村不可多得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在黄山工作。
1953年小弟也上小学,两个弟弟读书时就靠卖自留山上的木头解决费用问题。比经济压力还大的是从三年困难时期到1965年小弟高中毕业时的粮食困难,但家里再难也要让小弟能带米上学。兴华说,“两个弟弟有志读书,父亲不在了,这是我做大哥的应尽义务,家中再穷再困难也不能耽误弟弟的前途,何况他们两人读书都很用心。上中学以后,他们全靠政府资助享受助学金,我所起的作用也只有小小的一部分。能把两个弟弟培养成才,我也就对得起死去的父亲。”
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
听了朋友讲述的故事,真的很想去探望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农,看看他今天的生活和他一家人的情况。我托朋友捎个口信,表示我要拜访的意图。
一个烈日当头的上午,我像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东岙村,那天他正在整理一间二弟送给他的落顶屋,从苏州赶回来的小儿子和邻居帮他搬出里面笨重的老家具,准备把泥地改成水泥地面。只见他一身沾满灰尘的劳动衣,一头蓬乱的略花头发,仍不改山村老农的旧模样。我们的对话只能抽他休息间隙进行。
他是个多人口大户,老伴为他育有三女四儿。除了小儿子还未成家,其他子女都自立门户而去。他说老伴患病多年,现在已经能生活自理,全靠几个媳妇轮番照料。两个弟弟及子女都送钱送东西看望她。他自己也生过病,住过院,多亏有了农医保,减轻了自己的经济负担。我说你家里怎么还有毛主席这张伟人像,让你这么完好地保存到今天?他说,“这像原是小弟的,他搬家时我让他送的。现在当农民不用纳税交‘皇粮’, 水泥大道铺到村前,农民种田还有这补贴那优惠,我活了77年,也只有今天。毛主席是共产党领头人,留下作个老农民永远的纪念。”
我问他你家现在生活比你弟弟们差了些,你不觉得委屈吗?
兴华笑着说:“我们生活不及弟侄辈们,不是弟弟不尽心,这是不可强求的事。告诉你,我的三个孙子读书可争气呢。大孙女去年考入上海重点大学,二孙子小孙子在镇中读书,学习成绩都在年级15—30名之间,前途好着呢!”
“听说你现在还是过去老作风,一年到头不肯闲着?”
“老习惯了,一天不做,手酸腿软。坐在家里久了就会头昏脑胀,到田头走一走,头脑马上清醒。坐着不如走着,闲着不如做着。种点田地,就当活动筋骨锻炼身体,如今满担脚水可以一气挑到田头,医生说我身体健康一切正常。”说完他开心地笑了。
是的,一个善良又有责任心的人,他日思夜想的不是自己,考虑别人永远多于考虑个人。就像这位快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少年想的是为父亲弃学去挑家庭重担,青年时为培养兄弟甘愿付出辛勤汗水,老年了还叨念着孙辈们的学业,他的这辈子就这么一根弦,演奏的永远都是一个曲子——《亲人永远是我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