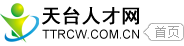“潘门石人”,即明代礼部尚书潘晟墓前的两对文、武官石像(又叫“石瓮仲”),当地人直称“石人”。潘晟墓址在三州乡政府所在地下屋村村外约1.5公里处,先后遭受多次破坏,石像除一尊被县博物馆收藏外,其余3尊于2009年被盗。
石人是三州群众记忆和情感寄托的地方
今年47岁的陈方亮在下屋村经营着一家肉店,说起石人,睡眼惺忪的陈方亮一骨碌爬了起来,陪笔者来到潘晟墓遗址前。
这是一个小山岙,两垅合抱,一片梯田,中间栽种的是茶树。这里是当地风水宝地,处于凤凰山“凤尾”上,又被称作潘门。从表面上看,丝毫发现不了这曾是达官贵人的最后居宿。
笔者跟着陈方亮来到其中一块茶地边,他指着一个高地说:“那里就是阁老的墓,从小时候到前几年一直都有人来盗挖。”当地人在称呼上,都称潘晟为潘阁老,因世代相传阁老是个好官。
然后,陈方亮指着茶地告诉笔者,那就是6年前4个石人摆放的位置。在他的记忆中,4个石人相向站立,靠里的是一对文官,头戴官帽,手执朝笏,宽袍大袖;外侧的武官则头戴钢盔,身披铠甲,柱剑而立。
陈方亮跳下茶地,找到一块岩石,告诉笔者这是其中一尊文官像的脚部。他比划着说,以他1.7米左右的个子,踮起来伸手还够不到石人的头顶。当时,石人小腿以下都埋在泥土里。照此估计,石像高度应在3米左右。
“石人没了,我们三州的仙气也没了。”陈方亮叹了口气。和绝大多数三州人一样,石人是三州群众记忆和情感寄托的地方。
缺乏必要的保护成了当地的一大心痛
“潘门的场面很大,除了石人,还有石马、石狗、石猪等,前面还有两对一大一小的望柱石,很风光很威严。”(下转第3版) (上接第1版)
“文革”期间,这宏大的场面消失了。望柱石被拆下造桥,损坏的石马石猪被砌了地坎,石人被炸药掀翻了一个,那弹石路、石板路被覆了土,种上了庄稼。
村民陈正虚在“潘门”这块地上已经耕种了十几年,在与石人为伴的日子里,“就是种地有些碍脚,但有了他们就好像不孤独了!”
有一段时间,经常有人来到他的地里打量石人,陈正虚说:“有的人是来看热闹,有的是来打石人主意的。”当时有人打算出价每个2万元购买石人,他以石人不是自己所有为由拒绝了对方,并把情况告诉了村里。
陈方标到过许多地方,知道石人的文物价值,他担心荒郊野外的石人会遭遇不测。他私下里也曾考虑,是不是由村里出面代行保管。但也有人认为,给石人挪了位置,它就不是“潘门石人”了。
6年前的一个雨夜,人们担忧已久的一幕终于降临了。除1个被盗走了头部的文官像外,另外3个石人销声匿迹,不知所踪。现场只留下几张起吊石人时包裹其外的棉被,及一条延伸了数百米远的车轮痕迹。
新媒体时代探寻民间追寻之路
“石人,你去哪儿了,乡亲们喊你回家……哪怕踏遍千山万水,哪怕探寻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找到你……如果我们老了,我们的子子孙孙将会继续,哪怕海枯石烂,哪怕天老地荒,直到找回你……”
王文浩道出了一个乡贤的肺腑之声。现在县教育局工作的王文浩,6年前曾在家乡任教,从小听到、看到许多和“潘门石人”有关的故事。
王文浩说:“小时候它让我感到很神秘,长大后它让我很牵挂,失去后我感到很不舍。”许多和王文浩一样的三州在外乡贤,对于石人的感情让他们急于找回因错过而失去的珍贵。
不久前,王文浩把自己的心声及2009年他带学生到潘晟墓旁的茶山上开展劳动实践用手机拍摄的10几幅石人照片交到三州乡党委书记张凯明手中。
3年前,张凯明由县政协调到三州乡,石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当时他的手头缺乏石人的详细图像资料,也缺乏有效的追寻方法。
“‘当时你们在干什么’。”张凯明明白,如果现在提出追寻石人,很可能会遭到质疑。但他说:“我们不用现在的标准来要求以前的。现在起步虽然晚了些,可是对我们来说,只要能把石人找回来,那比什么都重要。”
能不能在信息传播中找寻线索?张凯明认为借助自媒体的爆炸性扩散效应,值得一试。随后,该乡“三州地”微信公众号发出了民间“通缉令”,代表三州人民誓言找回乡民们的精神寄托,明确“追缉期限:直到永远,找到为止”。
三州乡民间“通缉令”在微友圈发布后,很快就成为网络上的一大热点。截至5月6日晚6点半,该乡已收到各类线索21条。(小徐 徐浩 吕超龙)